下面是索罗斯写的专栏“德国的选择”的长版.
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讨论欧元危机。根据最新发展,我想诸位都会同意,这场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危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和政治伤害,甚至还有不少人力损失。危机也把欧盟远远地推离了它的成立初衷。欧洲联盟本来意味着平等国家的自愿结盟,但危机把它分成了两个级层,德国和其他债权国主宰着重债国,并把后者打入了二等国家。尽管德国无法指定政策,但在实际中,如果不先得到德国的首肯,就没有哪项政策可以得以实施。更糟糕的是,德国所推行的紧缩政策起到了延长危机、使债务国沦为永久附庸的作用。
这造成了政治紧张局面,意大利的政治僵局就是明证。如今,意大利大部分人都反对欧盟,且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增强。现在,欧洲危机可能摧毁欧盟已成为现实威胁。无序的分裂给欧洲造成的伤害将大于创造欧盟的伟大实验开始时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历史悲剧。只有在德国的领导下才能避免这一悲剧。德国并未寻求过主导地位,也一直不愿接受领导地位所隐含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导致今天这个状态的原因之一。但不管德国情不情愿,驾驶员正是它,我站在这里演讲也是因为它。
欧洲怎样进入了这样一个乱局?又怎样摆脱它?这是我要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晦涩,因为欧元危机十分复杂。这个问题还有政治维度和金融维度。金融维度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以及竞争力分化。诸多角度相互联系,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晦涩,难以理解。在我看来,只有意识到错误和迷思在制造危机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欧元危机。这场危机几乎完全是自作自受。这堪称一场噩梦。
相反,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只要我们对问题有了正确的理解,解决方案就会自动浮出水面。
我得说,在制造危机的政策失误中,德国要背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我要进一步澄清,我并不是在指责德国。只要你居于主宰地位,就一定会犯下类似的错误。从个人经验出发,我可以说,没人可以在局势展开过程中完全认识到它的复杂性。
PS Events: AI Action Summit 2025
PS Events: AI Action Summit 2025
Don’t miss our next event, taking place at the AI Action Summit in Paris. Register now, and watch live on February 10 as leading thinkers consider what effective AI governance demands.
Register Now
我发现,我说德国必须担责或许会冒犯你们。但只有德国可以让事情走上正途。我是欧盟的坚定信仰者,我不希望看到它崩溃。我也关注着欧元危机造成的巨大的不必要的人身伤害,我愿意尽我所能减轻这一伤害。我对欧元危机的解读与德国流行的观点很不相同。我希望我能向你们提供不同的视角,让你们在伤害加深之前重新考虑你们的位置。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欧盟是一项大胆的工程,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大跌眼镜。我把欧盟看作开放社会的化身——平等国家自愿结盟,为了共同的利益交出部分主权。欧盟有五个大成员国和众多小成员国,它们都恪守民主原则、个人自由、人权和法治精神。不存在一国和一国身份把持主导地位的现象。
一体化过程的先锋是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们认识到,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他们实践的是卡尔•波普尔所谓的渐进性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他们为自己制定了有限的目标和明确的时间表,然后动员政治意愿以前进一小步。他们十分清楚,只要迈进了一小步,其不充分性就会显露无疑,从而要求迈进第二步。这一过程会自我增强,就像金融市场的枯荣循环。这就是煤炭和钢铁共同体一步一步转变为欧洲联盟的过程。
法国和德国曾是这一努力的先锋。当苏维埃帝国开始瓦解时,德国领导人意识到重新统一只有在更统一的欧洲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做好了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的准备。当讨价还价开始时,他们愿意比别人多付出,少收获,从而促成协定。当是时,德国政治家总是说,德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欧洲外交政策。这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在1990年德国统一以及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时达到了高潮。随之而来的是整合期,直到2007—08年金融危机爆发。
不幸的是,马约存在根本性缺陷。欧元的设计者意识到,这是个不完全的结构: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但是,欧元设计者有理由相信,当需要出现时,迈出新步伐的政治意愿可以被动员起来。毕竟,此前的一体化进程都是这样进行的。
但欧元还有其他诸多缺陷,不论是设计者还是成员国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比如,马约默认只有公共部门可能产生长期赤字,因为私人部门总是必须纠正其本身的过度行为。2007—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这是错误的。金融危机还揭露出欧元结构的一个近乎致命的缺陷:通过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成员国陷入了以它们无法控制的货币计价的债务。这让它们暴露在违约风险之中。
发达国家没有理由违约;它们总可以印钞。它们的货币可以编制,但违约风险实际并不存在。相反,必须借入外币债务的欠发达地区有违约的风险。更糟糕的是,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做空袭击致使这类国家违约。违约风险把一些成员国打入了外币债务深重国的第三世界。
在2007—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当局和金融市场都忽视了欧元的这一特征。引入欧元时,政府债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监管者允许商业银行买入无限量的政府债券而不需要为此拔备任何股本,而欧洲中央银行在其贴现窗口接受所有政府债券并对它们一视同仁。这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负面激励,它们囤积利率更高的疲软成员国债券以赚取几个额外基点。结果,不同政府债券间的利率差异实际消失了。
利率的趋同导致了经济表现的趋异。所谓的外围国——主要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享受了削弱竞争力的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繁荣,而饱受重新统一成本困扰德国实施了深刻的劳动力上苍和其他结构性改革,增强了竞争力。
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这一周,全球金融市场几乎瘫痪,需要生命支持仪才能继续运转。这需要以主权信用(其形式为央行担保和预算赤字)替换饱受重创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对主权信用的强调凸显出迄今仍被忽视的欧元特征,即通过成立独立中央银行,欧元成员国交出了部分主权。
这本是迈出通往财政和货币联盟新步伐的时刻,但政治意愿却没有了。承受了重新统一巨大成本的德国不再是一体化的先锋。总理默克尔正确地领悟了民意,宣布各国应该自己看好自己的金融机构,而不是期待欧盟的集体行动。这是倒退。事后看去,这是分裂过程的开端。
金融市场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意识到默克尔的决定的影响,这表明金融市场也在以远远称不上完美的知识在运行。直到2009年底希腊赤字状况真相大白后,金融市场才意识到成员国也可能违约。但随后上市场报复性地提高了疲软国的风险溢价。这不啻宣布资产负债表满载这些债券的商业银行实际破产,从而造成了主权债务和银行双重危机。这两大危机是连体双胞胎。
欧元危机和1982年国际银行危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当年,IMF和国际银行当局通过向重债国提供足够贷款使它们避免违约拯救了国际银行系统,但代价是让它们陷入了持续萧条。拉丁美洲因此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今天,德国的角色与当年的IMF相同。今时与往日条件有异,但效果相同。债权国事实上再将整个调整负担转移给债务国,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失衡责任。有趣的是,“中心”和“外围”等词几乎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了人们的适用范围,尽管从政治上讲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描述为欧盟外围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事实上,欧元已将它们的政府债券打入了有违约风险的第三世界国家等级。这一事实被当局所忽视,至今认为得到应有的认识。这就是欧元危机的根源。
和20世纪80年代一样,落在“外围”头上的所有指责和负担以及“中心”的责任从来没有获得过合理的承认。外围国被批评缺少财政纪律和工作道德,但这并不是全部。诚然,外围国家需要结构性改革,一如德国在重新统一后那样。但否认欧元本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纠正无异于忽视欧元危机的根源。但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从这个方面讲,德语词汇“罪责”(Schuld)起着关键作用。大家知道,这个词既有债务和责任的意思,也有罪恶的意思。这个词让德国指责重债国罪有应得的民意变得十分自然或“不证自明”(selbstverständlich)。希腊公然违反规则的事实也支持这一态度。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其他国家一直遵守着规则;事实上西班牙还因为是守规矩的典范而得到了援助。显然,缺陷是系统性的,重债国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拜欧元治理规则所赐。这就是我今天想澄清的一点。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心”的“罪责”或责任比1982年银行危机时还要深重。1982年要求欠发达国家实施紧缩以拯救国际金融系统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但今天在欧元区内部重施故技与欧盟作为平等国家的自愿结合的性质格格不入。在金融上必要与在政治上可接受之间存在有待解决的矛盾。最近的意大利选举应该让我们看清了这一点。
责任的重担主要落在德国头上。德国联邦银行协助设计了欧元,而欧元的缺陷把德国推上了掌舵者的位置。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金融上的。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让局面变得极为棘手。
政治问题是,德国并未寻求充当它被推上的掌舵位置,它也不愿意接受掌舵位置带来的义务和责任。不难理解,德国不愿意成为欧元的“提款机”。因此它它只提供堪堪足以避免委员的支持,除此之外便不愿做得更多,而一等到金融市场压力减缓,它就开始寻求收紧支持条件。
金融问题是,德国再给欧元区施加错误的政策。紧缩是无效的。你不可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减少债务负担。债务负担是累积债务和GDP的比率,两者都是名义值。而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削减预算会引起GDP下降更快——用术语讲,就是所谓的财政乘数大于1。
德国公众难以理解这一点。施罗德政府所实施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2006年起效过;为何不能在几年后在欧元区起效?答案在于紧缩是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起效的。当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它就不可能起效。
欧元危机在去年夏天达到了顶峰。金融市场开始预测可能的解体,风险溢价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水平。默克尔总理最后不得不支持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放弃了她自己的提名人魏德曼。德拉吉有能力应对这一危局。他宣布欧洲央行将“竭尽全力”捍卫欧元,并通过引入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支持欧元。金融市场放了心,出现了剧烈的安慰性反弹。但别高兴得太早了。金融市场压力一缓解,德国就开始降格其在危机高峰期所做的承诺。
在援助塞浦路斯的过程中,德国走得太远了。为了让援助成本最小化,德国坚持要银行储户自救。这操之过急了。如果这发生在银行联盟成立、银行获得资本重组之后,那么或许是健康的发展方向。但德国却要求在银行系统正在耗尽国家资源且依然十分脆弱时这样做。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情破坏了欧洲银行的业务模式,即严重依赖存款。直到如今,当局还在寻找保护储户之道。塞浦路斯改变了这一点。注意力被集中于援助塞浦路斯的影响,但银行系统的影响要重要得多。银行将必须付出风险溢价,而疲软银行和疲软国银行所付出的的风险溢价负担会高得多。主权债务成本和银行债务成本之间的隐藏联系将得到加强。游戏规则将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公。
默克尔总理将放任欧元区危机发展,至少在选举之前是如此,但局面正在反弹。德国公众可能已经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塞浦路斯是默克尔总理的一次政治大胜。没有国家敢于对她的想法说不。此外,德国本身相对而言并未受席卷欧元区的深化的危机的影响。不过,我预计到进行选举时,德国也将进入衰退。这是因为,欧元区所追求的货币政策与其他主要货币不同步。其他货币纷纷实行着量化宽松。日本银行是最后一块顽石,但最近也转换了立场。贬值的日元加上欧洲的弱势,注定会影响德国的出口。
如果我的分析正确,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便自动浮出了水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欧元债券。
欧元债券所有成员国的连带义务。如果遵守财政契约的国家可以将所有政府债务存量转为欧元债券,其积极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违约风险将消失,风险溢价也随之而逝。银行资产负债表立刻可以获得提振,重债国的预算也将马上改善,因为它们对现有政府债务付息的成本立刻下降了。比如,意大利将最多剩下GDP的4%。其预算将出现盈余,政府将不再需要紧缩,可以实施财政刺激。经济将增长,债务比率将下降。大部分看似棘手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唯一剩下的问题是竞争力分化。个别国家将仍需要结构性改革,但欧元的主要结构缺陷将得到纠正。这一方案堪称从噩梦中苏醒。
财政契约为连带责任所包含的风险提供了足够的保护。根据财政契约,成员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发行新债券,即取代到期债券;五年后,未到期存量债券将逐渐降至GDP的60%。如果一国不遵守契约,它将受到惩罚,其可发行欧元债券数量将被限制;它将以自身的名义借款,付出高昂的风险溢价。
德国反对欧元债券。它的理由是,一旦引入欧元债券,无法保证所谓的外围国不会再次破坏规定。我认为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被剥夺发行欧元债券的权利、被迫偿付极其高昂的风险溢价,这已是遵守规定的强大激励。事实上,惩罚是非常严酷的,甚至可能会有不要出手过重的呼声,以免触犯国的金融状况突然恶化。与此同时,一个主事的财政当局将执行更严格的控制,违抗财政当局将被罚以进一步减少欧元债券允许发行量。没有哪个政府经得起如此压力。
另一个普遍的担忧是欧元债券会损害德国的信用评级。欧元债券经常被拿来与马歇尔计划比较。这个观点认为,马歇尔计划只耗费了美国GDP的几个百分点,而欧元债券将耗费德国GDP的数倍。这纯属拿橘子和苹果比。马歇尔计划是实打实的支出,而欧元债券只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支出的担保。德国同意欧元债券的代价被大大夸大了。
担保有一个独特的特征:越是可信,就越不可能触发担保事件。美国曾将个别州的债务转换为联邦债务,但从未为此债务付出过真金白银。德国一直只愿意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这正是它不得不不断升级承诺并遭受实际损失的原因。以运转良好的财政当局为支撑的财政契约将从事实上消除违约风险。欧元债券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与美国、英国和日本债券等量齐观。诚然,德国自身将必须付出比今天更多的债务偿付,但德国国债的出奇低收益率乃是外围国病症的症候。外围国复苏给德国带来的间接好处将远远高于其自身国民债务成本的增加。
平心而论,欧元债券并非万灵丹。首先,财政契约本身是个有设计缺陷的工具。欧元债券的引入能提振欧元区,但可能效果并不足够。果真如此的话,就需要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但能有这样的问题也是一种奢侈。
其次,欧盟也需要银行联盟,最终需要政治联盟。塞浦路斯援助凸显出欧洲银行严重依赖大储户的业务模式问题,让这一需要更加迫切了。
欧元债券的主要局限是,它无法抹除竞争力之间的差异。个别国家将仍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不这样做的国家将滑入永久性贫困和附属地位,很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它们将靠来自欧洲结构性基金和侨汇的有限支持生存。但德国接受欧元债券将彻底改变政治气氛,有利于实施同样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的事实依然是大部分德国公众强烈反对欧元债券。自默克尔总理否决欧元债券以来,我所提出的观点甚至不曾得到过考虑。人们没有意识到,批准欧元债券比以最低限度努力维持欧元的成本低得多。
是否愿意授权欧元债券取决于德国。但德国无权阻止重债国抱团发行欧元债券自救。换句话说,如果德国反对欧元债券,它就应该考虑退出欧元,让其他国家来推出欧元债券。
如此行事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没有德国的欧元区所发行的欧元债券仍然能够与美国、英国和日本债券等量齐观。上述三国的净债务占GDP比率实际上比没有德国的欧元区还要高。
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可以通过比较德国退出欧元和某重债国(如意大利)退出欧元的后果来解释。
由于所有累积债务都是用欧元计价的,因此由哪个国家主导欧元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德国退出,则欧元将贬值。债务国将重新获得竞争力。它们的债务真实值将减少,而如果发行了欧元债券,违约风险也将消失。它们的债务一夜之间变成可持续的。大部分调整的负担将落在退出欧元的国家头上。他们的出口将失去竞争力,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将面临来自欧元区的激烈竞争。它们的欧元计价债权和投资也将遭受损失。损失的程度取决于欧元贬值的程度;因此将贬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符合它们的利益。在最初的偏移之后,最终的结果将满足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之梦——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维持稳定的责任。欧洲也将摆脱萧条阴影。
相反,如果意大利退出,其欧元计价债务负担将变得不可持续,不得不进行重组。这将动摇欧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造成金融崩溃,货币当局根本无力治理这一乱局。欧元的崩溃很有可能造成欧盟的无序分裂,而欧洲的境况将比它开始欧盟的伟大实验之前更加糟糕。
显然,退出欧元对德国比对意大利更好;同样显然的是,对德国来说,批准欧元比退出欧元更好。麻烦在于,德国还没有到被迫做出选择的时候,它还有一套替代方案:它可以放任现状自流,总是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维持欧元,除此之外再无举措。
如果我的分析正确,那么即便对于德国,这也不是最佳方案,除非你只看短期。局面在恶化,最终注定将不可持续。拖得越久,伤害越大。尽管如此,这却是德国更为偏好的选择,至少在选举之前是如此。
德国要在批准欧元债券和退出欧元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这是一件大事,也是我来这里参与讨论的目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深思,应该现在亮明我的看法还是等到选举之后。最后我决定先下手,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事情有其自身动态,危机可能在选举之前进一步恶化。塞浦路斯援助行动证明我是正确的。二是我对事件的解读与德国的普遍看法大大相悖,我的解读被理解需要时间,而我越早开始越好。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德国在欧元债券和退出欧元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继续按现在的做法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维系欧元,欧洲的境况将会有所改善。不管德国批准欧元还是退出欧元都是如此;且不但对欧洲是如此,对德国也是如此,除非你只看极短期。
对德国而言,这两个选择孰优孰劣尚不清楚。只有德国选民有资格作出决定。如果今天举行公投,那么欧元怀疑派将轻松获胜。但更透彻的考虑可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他们会发现,德国授权欧元债券的代价被大大夸大了,而退出欧元的代价被低估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选择是欧元债券,第二选择是德国退出欧元。不管哪个选择,都远远好于不做选择而让危机持续。最坏的情景是债务国(比如意大利)退出欧元,因为这会导致欧盟的无序解体。
我的结论有些出人意料,特别是关于欧元债券在没有德国的情况下仍堪称完美的论断。我的亲欧洲朋友们对此表示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没有德国的欧元。我认为他们是将欧元和欧盟混为一谈了。这两者并不相同。欧盟是目标,而欧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不能允许欧元摧毁欧盟。
但我的分析或许过于理性了。将欧盟和欧元混为一谈,不仅普罗大众是如此,法律条文也是如此。于是,德国退出欧元,欧盟就无法生存。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得竭尽全力说服德国公众抛弃其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迷思,接受欧元债券。
最后,我想强调,欧盟不仅对欧洲重要,对全世界也是如此。欧盟是开放社会原则的天然化身。这意味着完美知识的不可获得性。没人能摆脱偏见和迷思;没人应该因错误而受人指责。指责和罪责只能产生于错误和迷思被发现而不是被纠正之时,即破坏了作为欧盟基石的原则之时。正因如此,德国应该批准欧元债券,拯救欧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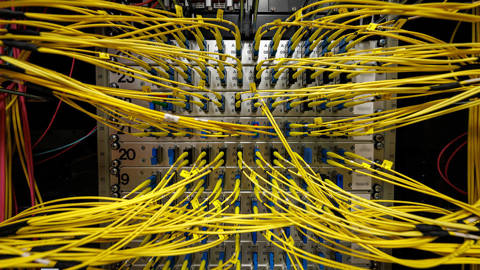

下面是索罗斯写的专栏“德国的选择”的长版.
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讨论欧元危机。根据最新发展,我想诸位都会同意,这场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危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和政治伤害,甚至还有不少人力损失。危机也把欧盟远远地推离了它的成立初衷。欧洲联盟本来意味着平等国家的自愿结盟,但危机把它分成了两个级层,德国和其他债权国主宰着重债国,并把后者打入了二等国家。尽管德国无法指定政策,但在实际中,如果不先得到德国的首肯,就没有哪项政策可以得以实施。更糟糕的是,德国所推行的紧缩政策起到了延长危机、使债务国沦为永久附庸的作用。
这造成了政治紧张局面,意大利的政治僵局就是明证。如今,意大利大部分人都反对欧盟,且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增强。现在,欧洲危机可能摧毁欧盟已成为现实威胁。无序的分裂给欧洲造成的伤害将大于创造欧盟的伟大实验开始时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历史悲剧。只有在德国的领导下才能避免这一悲剧。德国并未寻求过主导地位,也一直不愿接受领导地位所隐含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导致今天这个状态的原因之一。但不管德国情不情愿,驾驶员正是它,我站在这里演讲也是因为它。
欧洲怎样进入了这样一个乱局?又怎样摆脱它?这是我要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晦涩,因为欧元危机十分复杂。这个问题还有政治维度和金融维度。金融维度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以及竞争力分化。诸多角度相互联系,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晦涩,难以理解。在我看来,只有意识到错误和迷思在制造危机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欧元危机。这场危机几乎完全是自作自受。这堪称一场噩梦。
相反,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只要我们对问题有了正确的理解,解决方案就会自动浮出水面。
我得说,在制造危机的政策失误中,德国要背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我要进一步澄清,我并不是在指责德国。只要你居于主宰地位,就一定会犯下类似的错误。从个人经验出发,我可以说,没人可以在局势展开过程中完全认识到它的复杂性。
PS Events: AI Action Summit 2025
Don’t miss our next event, taking place at the AI Action Summit in Paris. Register now, and watch live on February 10 as leading thinkers consider what effective AI governance demands.
Register Now
我发现,我说德国必须担责或许会冒犯你们。但只有德国可以让事情走上正途。我是欧盟的坚定信仰者,我不希望看到它崩溃。我也关注着欧元危机造成的巨大的不必要的人身伤害,我愿意尽我所能减轻这一伤害。我对欧元危机的解读与德国流行的观点很不相同。我希望我能向你们提供不同的视角,让你们在伤害加深之前重新考虑你们的位置。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欧盟是一项大胆的工程,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大跌眼镜。我把欧盟看作开放社会的化身——平等国家自愿结盟,为了共同的利益交出部分主权。欧盟有五个大成员国和众多小成员国,它们都恪守民主原则、个人自由、人权和法治精神。不存在一国和一国身份把持主导地位的现象。
一体化过程的先锋是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们认识到,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他们实践的是卡尔•波普尔所谓的渐进性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他们为自己制定了有限的目标和明确的时间表,然后动员政治意愿以前进一小步。他们十分清楚,只要迈进了一小步,其不充分性就会显露无疑,从而要求迈进第二步。这一过程会自我增强,就像金融市场的枯荣循环。这就是煤炭和钢铁共同体一步一步转变为欧洲联盟的过程。
法国和德国曾是这一努力的先锋。当苏维埃帝国开始瓦解时,德国领导人意识到重新统一只有在更统一的欧洲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做好了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的准备。当讨价还价开始时,他们愿意比别人多付出,少收获,从而促成协定。当是时,德国政治家总是说,德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欧洲外交政策。这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一进程在1990年德国统一以及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时达到了高潮。随之而来的是整合期,直到2007—08年金融危机爆发。
不幸的是,马约存在根本性缺陷。欧元的设计者意识到,这是个不完全的结构: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但是,欧元设计者有理由相信,当需要出现时,迈出新步伐的政治意愿可以被动员起来。毕竟,此前的一体化进程都是这样进行的。
但欧元还有其他诸多缺陷,不论是设计者还是成员国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比如,马约默认只有公共部门可能产生长期赤字,因为私人部门总是必须纠正其本身的过度行为。2007—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这是错误的。金融危机还揭露出欧元结构的一个近乎致命的缺陷:通过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成员国陷入了以它们无法控制的货币计价的债务。这让它们暴露在违约风险之中。
发达国家没有理由违约;它们总可以印钞。它们的货币可以编制,但违约风险实际并不存在。相反,必须借入外币债务的欠发达地区有违约的风险。更糟糕的是,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做空袭击致使这类国家违约。违约风险把一些成员国打入了外币债务深重国的第三世界。
在2007—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当局和金融市场都忽视了欧元的这一特征。引入欧元时,政府债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监管者允许商业银行买入无限量的政府债券而不需要为此拔备任何股本,而欧洲中央银行在其贴现窗口接受所有政府债券并对它们一视同仁。这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负面激励,它们囤积利率更高的疲软成员国债券以赚取几个额外基点。结果,不同政府债券间的利率差异实际消失了。
利率的趋同导致了经济表现的趋异。所谓的外围国——主要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享受了削弱竞争力的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繁荣,而饱受重新统一成本困扰德国实施了深刻的劳动力上苍和其他结构性改革,增强了竞争力。
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这一周,全球金融市场几乎瘫痪,需要生命支持仪才能继续运转。这需要以主权信用(其形式为央行担保和预算赤字)替换饱受重创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对主权信用的强调凸显出迄今仍被忽视的欧元特征,即通过成立独立中央银行,欧元成员国交出了部分主权。
这本是迈出通往财政和货币联盟新步伐的时刻,但政治意愿却没有了。承受了重新统一巨大成本的德国不再是一体化的先锋。总理默克尔正确地领悟了民意,宣布各国应该自己看好自己的金融机构,而不是期待欧盟的集体行动。这是倒退。事后看去,这是分裂过程的开端。
金融市场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意识到默克尔的决定的影响,这表明金融市场也在以远远称不上完美的知识在运行。直到2009年底希腊赤字状况真相大白后,金融市场才意识到成员国也可能违约。但随后上市场报复性地提高了疲软国的风险溢价。这不啻宣布资产负债表满载这些债券的商业银行实际破产,从而造成了主权债务和银行双重危机。这两大危机是连体双胞胎。
欧元危机和1982年国际银行危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当年,IMF和国际银行当局通过向重债国提供足够贷款使它们避免违约拯救了国际银行系统,但代价是让它们陷入了持续萧条。拉丁美洲因此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今天,德国的角色与当年的IMF相同。今时与往日条件有异,但效果相同。债权国事实上再将整个调整负担转移给债务国,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失衡责任。有趣的是,“中心”和“外围”等词几乎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了人们的适用范围,尽管从政治上讲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描述为欧盟外围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事实上,欧元已将它们的政府债券打入了有违约风险的第三世界国家等级。这一事实被当局所忽视,至今认为得到应有的认识。这就是欧元危机的根源。
和20世纪80年代一样,落在“外围”头上的所有指责和负担以及“中心”的责任从来没有获得过合理的承认。外围国被批评缺少财政纪律和工作道德,但这并不是全部。诚然,外围国家需要结构性改革,一如德国在重新统一后那样。但否认欧元本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纠正无异于忽视欧元危机的根源。但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从这个方面讲,德语词汇“罪责”(Schuld)起着关键作用。大家知道,这个词既有债务和责任的意思,也有罪恶的意思。这个词让德国指责重债国罪有应得的民意变得十分自然或“不证自明”(selbstverständlich)。希腊公然违反规则的事实也支持这一态度。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其他国家一直遵守着规则;事实上西班牙还因为是守规矩的典范而得到了援助。显然,缺陷是系统性的,重债国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拜欧元治理规则所赐。这就是我今天想澄清的一点。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心”的“罪责”或责任比1982年银行危机时还要深重。1982年要求欠发达国家实施紧缩以拯救国际金融系统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但今天在欧元区内部重施故技与欧盟作为平等国家的自愿结合的性质格格不入。在金融上必要与在政治上可接受之间存在有待解决的矛盾。最近的意大利选举应该让我们看清了这一点。
责任的重担主要落在德国头上。德国联邦银行协助设计了欧元,而欧元的缺陷把德国推上了掌舵者的位置。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金融上的。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让局面变得极为棘手。
政治问题是,德国并未寻求充当它被推上的掌舵位置,它也不愿意接受掌舵位置带来的义务和责任。不难理解,德国不愿意成为欧元的“提款机”。因此它它只提供堪堪足以避免委员的支持,除此之外便不愿做得更多,而一等到金融市场压力减缓,它就开始寻求收紧支持条件。
金融问题是,德国再给欧元区施加错误的政策。紧缩是无效的。你不可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减少债务负担。债务负担是累积债务和GDP的比率,两者都是名义值。而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削减预算会引起GDP下降更快——用术语讲,就是所谓的财政乘数大于1。
德国公众难以理解这一点。施罗德政府所实施的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2006年起效过;为何不能在几年后在欧元区起效?答案在于紧缩是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起效的。当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它就不可能起效。
欧元危机在去年夏天达到了顶峰。金融市场开始预测可能的解体,风险溢价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水平。默克尔总理最后不得不支持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放弃了她自己的提名人魏德曼。德拉吉有能力应对这一危局。他宣布欧洲央行将“竭尽全力”捍卫欧元,并通过引入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支持欧元。金融市场放了心,出现了剧烈的安慰性反弹。但别高兴得太早了。金融市场压力一缓解,德国就开始降格其在危机高峰期所做的承诺。
在援助塞浦路斯的过程中,德国走得太远了。为了让援助成本最小化,德国坚持要银行储户自救。这操之过急了。如果这发生在银行联盟成立、银行获得资本重组之后,那么或许是健康的发展方向。但德国却要求在银行系统正在耗尽国家资源且依然十分脆弱时这样做。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事情破坏了欧洲银行的业务模式,即严重依赖存款。直到如今,当局还在寻找保护储户之道。塞浦路斯改变了这一点。注意力被集中于援助塞浦路斯的影响,但银行系统的影响要重要得多。银行将必须付出风险溢价,而疲软银行和疲软国银行所付出的的风险溢价负担会高得多。主权债务成本和银行债务成本之间的隐藏联系将得到加强。游戏规则将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公。
默克尔总理将放任欧元区危机发展,至少在选举之前是如此,但局面正在反弹。德国公众可能已经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塞浦路斯是默克尔总理的一次政治大胜。没有国家敢于对她的想法说不。此外,德国本身相对而言并未受席卷欧元区的深化的危机的影响。不过,我预计到进行选举时,德国也将进入衰退。这是因为,欧元区所追求的货币政策与其他主要货币不同步。其他货币纷纷实行着量化宽松。日本银行是最后一块顽石,但最近也转换了立场。贬值的日元加上欧洲的弱势,注定会影响德国的出口。
如果我的分析正确,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便自动浮出了水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欧元债券。
欧元债券所有成员国的连带义务。如果遵守财政契约的国家可以将所有政府债务存量转为欧元债券,其积极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违约风险将消失,风险溢价也随之而逝。银行资产负债表立刻可以获得提振,重债国的预算也将马上改善,因为它们对现有政府债务付息的成本立刻下降了。比如,意大利将最多剩下GDP的4%。其预算将出现盈余,政府将不再需要紧缩,可以实施财政刺激。经济将增长,债务比率将下降。大部分看似棘手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唯一剩下的问题是竞争力分化。个别国家将仍需要结构性改革,但欧元的主要结构缺陷将得到纠正。这一方案堪称从噩梦中苏醒。
财政契约为连带责任所包含的风险提供了足够的保护。根据财政契约,成员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发行新债券,即取代到期债券;五年后,未到期存量债券将逐渐降至GDP的60%。如果一国不遵守契约,它将受到惩罚,其可发行欧元债券数量将被限制;它将以自身的名义借款,付出高昂的风险溢价。
德国反对欧元债券。它的理由是,一旦引入欧元债券,无法保证所谓的外围国不会再次破坏规定。我认为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被剥夺发行欧元债券的权利、被迫偿付极其高昂的风险溢价,这已是遵守规定的强大激励。事实上,惩罚是非常严酷的,甚至可能会有不要出手过重的呼声,以免触犯国的金融状况突然恶化。与此同时,一个主事的财政当局将执行更严格的控制,违抗财政当局将被罚以进一步减少欧元债券允许发行量。没有哪个政府经得起如此压力。
另一个普遍的担忧是欧元债券会损害德国的信用评级。欧元债券经常被拿来与马歇尔计划比较。这个观点认为,马歇尔计划只耗费了美国GDP的几个百分点,而欧元债券将耗费德国GDP的数倍。这纯属拿橘子和苹果比。马歇尔计划是实打实的支出,而欧元债券只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支出的担保。德国同意欧元债券的代价被大大夸大了。
担保有一个独特的特征:越是可信,就越不可能触发担保事件。美国曾将个别州的债务转换为联邦债务,但从未为此债务付出过真金白银。德国一直只愿意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这正是它不得不不断升级承诺并遭受实际损失的原因。以运转良好的财政当局为支撑的财政契约将从事实上消除违约风险。欧元债券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与美国、英国和日本债券等量齐观。诚然,德国自身将必须付出比今天更多的债务偿付,但德国国债的出奇低收益率乃是外围国病症的症候。外围国复苏给德国带来的间接好处将远远高于其自身国民债务成本的增加。
平心而论,欧元债券并非万灵丹。首先,财政契约本身是个有设计缺陷的工具。欧元债券的引入能提振欧元区,但可能效果并不足够。果真如此的话,就需要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但能有这样的问题也是一种奢侈。
其次,欧盟也需要银行联盟,最终需要政治联盟。塞浦路斯援助凸显出欧洲银行严重依赖大储户的业务模式问题,让这一需要更加迫切了。
欧元债券的主要局限是,它无法抹除竞争力之间的差异。个别国家将仍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不这样做的国家将滑入永久性贫困和附属地位,很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它们将靠来自欧洲结构性基金和侨汇的有限支持生存。但德国接受欧元债券将彻底改变政治气氛,有利于实施同样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的事实依然是大部分德国公众强烈反对欧元债券。自默克尔总理否决欧元债券以来,我所提出的观点甚至不曾得到过考虑。人们没有意识到,批准欧元债券比以最低限度努力维持欧元的成本低得多。
是否愿意授权欧元债券取决于德国。但德国无权阻止重债国抱团发行欧元债券自救。换句话说,如果德国反对欧元债券,它就应该考虑退出欧元,让其他国家来推出欧元债券。
如此行事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没有德国的欧元区所发行的欧元债券仍然能够与美国、英国和日本债券等量齐观。上述三国的净债务占GDP比率实际上比没有德国的欧元区还要高。
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可以通过比较德国退出欧元和某重债国(如意大利)退出欧元的后果来解释。
由于所有累积债务都是用欧元计价的,因此由哪个国家主导欧元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德国退出,则欧元将贬值。债务国将重新获得竞争力。它们的债务真实值将减少,而如果发行了欧元债券,违约风险也将消失。它们的债务一夜之间变成可持续的。大部分调整的负担将落在退出欧元的国家头上。他们的出口将失去竞争力,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将面临来自欧元区的激烈竞争。它们的欧元计价债权和投资也将遭受损失。损失的程度取决于欧元贬值的程度;因此将贬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符合它们的利益。在最初的偏移之后,最终的结果将满足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之梦——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维持稳定的责任。欧洲也将摆脱萧条阴影。
相反,如果意大利退出,其欧元计价债务负担将变得不可持续,不得不进行重组。这将动摇欧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造成金融崩溃,货币当局根本无力治理这一乱局。欧元的崩溃很有可能造成欧盟的无序分裂,而欧洲的境况将比它开始欧盟的伟大实验之前更加糟糕。
显然,退出欧元对德国比对意大利更好;同样显然的是,对德国来说,批准欧元比退出欧元更好。麻烦在于,德国还没有到被迫做出选择的时候,它还有一套替代方案:它可以放任现状自流,总是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维持欧元,除此之外再无举措。
如果我的分析正确,那么即便对于德国,这也不是最佳方案,除非你只看短期。局面在恶化,最终注定将不可持续。拖得越久,伤害越大。尽管如此,这却是德国更为偏好的选择,至少在选举之前是如此。
德国要在批准欧元债券和退出欧元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这是一件大事,也是我来这里参与讨论的目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深思,应该现在亮明我的看法还是等到选举之后。最后我决定先下手,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事情有其自身动态,危机可能在选举之前进一步恶化。塞浦路斯援助行动证明我是正确的。二是我对事件的解读与德国的普遍看法大大相悖,我的解读被理解需要时间,而我越早开始越好。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德国在欧元债券和退出欧元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继续按现在的做法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维系欧元,欧洲的境况将会有所改善。不管德国批准欧元还是退出欧元都是如此;且不但对欧洲是如此,对德国也是如此,除非你只看极短期。
对德国而言,这两个选择孰优孰劣尚不清楚。只有德国选民有资格作出决定。如果今天举行公投,那么欧元怀疑派将轻松获胜。但更透彻的考虑可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他们会发现,德国授权欧元债券的代价被大大夸大了,而退出欧元的代价被低估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选择是欧元债券,第二选择是德国退出欧元。不管哪个选择,都远远好于不做选择而让危机持续。最坏的情景是债务国(比如意大利)退出欧元,因为这会导致欧盟的无序解体。
我的结论有些出人意料,特别是关于欧元债券在没有德国的情况下仍堪称完美的论断。我的亲欧洲朋友们对此表示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没有德国的欧元。我认为他们是将欧元和欧盟混为一谈了。这两者并不相同。欧盟是目标,而欧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不能允许欧元摧毁欧盟。
但我的分析或许过于理性了。将欧盟和欧元混为一谈,不仅普罗大众是如此,法律条文也是如此。于是,德国退出欧元,欧盟就无法生存。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得竭尽全力说服德国公众抛弃其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迷思,接受欧元债券。
最后,我想强调,欧盟不仅对欧洲重要,对全世界也是如此。欧盟是开放社会原则的天然化身。这意味着完美知识的不可获得性。没人能摆脱偏见和迷思;没人应该因错误而受人指责。指责和罪责只能产生于错误和迷思被发现而不是被纠正之时,即破坏了作为欧盟基石的原则之时。正因如此,德国应该批准欧元债券,拯救欧盟。